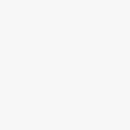最近有部劇把我攥得手心冒汗——父親開了兩個女兒包。演員表里的每個名字都壓著熱氣,尤其是父女對峙的戲碼,像鐵錘砸在心口,蹦出的火星全是我認得的疼。導演把愛寫成鈍器,鈍得往下砸時連空氣都跟著凝滯,可那鈍里頭裹著錐心的鈍,鈍得人心里全都是鮮血橫流的轟響。
 一、演員表里的血肉,都活在刀尖上
一、演員表里的血肉,都活在刀尖上
看演員表時我先算了算年份:父親的演員比女兒大三輪,可臺詞里全是永恒的差一年零一個月。女兒說"爸你該娶個能伺候你的人",話音剛落,父親的喉結就動了三下;鏡頭給到演員表里配戲的女仆時,她舉茶杯的動作里摻著十二分的冷淡。
父子關系那層皮剝開是血淋漓的薄脆,父親給養女掖被角時手背青筋暴起,這種暴不是憤怒,是血脈在竄。女兒演員哭戲全壓在后槽牙,眼淚珠子滾下來硬生生碾碎成霧,像極了活吞苦果的人。
二、愛是把人逼成瘋子的清醒劑劇里頭最要命的,是父親為了兩個女兒包的長相去做硅膠手術。手術室那場戲,碘伏味能從熒幕里洇出來。扮演醫生的演員扣動脈鉗時,指節泛著冷青,而父親演員的嘴皮子早凍成霜,唯獨眼眶發著紫。
女兒在閣樓里燒骨灰盒的段落,火焰啃噬紙盒的聲音比心跳還清晰。她說"我不要這世上還有另一個我",可鏡子里映出的側臉輪廓,活脫脫是另一個她十五歲的模樣。演員演到這兒時,連呼吸都成了劇中人,跟觀眾隔了層薄玻璃對峙。
三、這部劇有多真實,就有多扎人看時腦門子后頭總跟扎著個刺猬似的,特別是拍到父親對著陰陽盆念悼詞那場。他念著"兒啊"時,聲音拐進氣管里嗆出痰音,這種自洽的痛苦讓人想起鄰居家修自行車的老王,他也總對著拐角那棵枯槐樹叨叨叨。
女兒演員把叛逆捏成團在手里揉來揉去,直到那團子融進皮膚里開出痘。她說"我要告你"時眼神浮著油,可隔五分鐘回頭再看父親領口的紐扣,她就把食指戳進肉里青了。這種度量差的處理,比現實主義還現實。
四、的火車汽笛聲,比哭聲更揪心最后一集的音效處理教人記不得臺詞,只記得火車輪過鐵軌的哐當聲。父親站在站臺上遞飯盒,女兒接過的瞬間他們的鼻尖差兩分錢碰到,鏡頭切到演員表里的群眾演員時,全都是側臉。
這種留白像極了街邊賣糖人的老漢,舀子剛揚起來糖漿就停在空中。你看著鐵軌延伸到天盡頭,看著父女影子越拉越長,直到認不出是誰是誰。
追著這部劇追到鍵盤敲出水,倒不是為了看演員表里那幾張臉,是想看骨子里的親人情怎么腌進膠片。導演說要拍出割心的愛,可誰想看見心在砧板上切來剁去?最后發現最戳人的不是眼淚,是演員表里那些人把血肉往砧板上捺時,你突然想起自家飯桌角落那個皺巴巴的塑料袋——里頭裝的,興許也是類似的鈍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