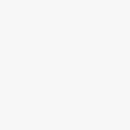血色月光下,手術(shù)燈驟亮時,我看見他從消毒單下探出的手指。骨節(jié)分明如刀鋒,指節(jié)上的紋路深深嵌進掌心,卻又被輸液管與監(jiān)控探頭纏繞得像條困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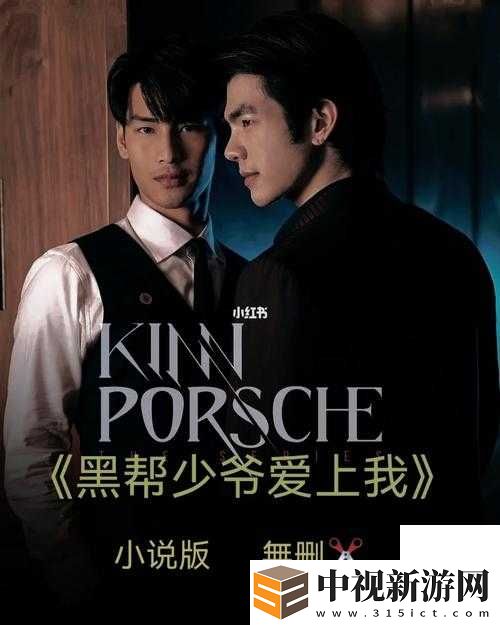
這是我加入圣約翰醫(yī)院第三年首次遇見霍世安。急診科的晝夜輪轉(zhuǎn)中,形形**的傷員像被切割的拼圖般滾進平躺的鐵床。唯有那條蒼白的手臂令我想起深冬湖面漂浮的殘雪,在暖黃燈光里泛著寒氣。
護士站傳來急促的熒光警報,導管室的門鏡反射著紅光。我摘下口罩快步穿過走廊,消毒水味道混著血腥氣撲面而來。推床在轉(zhuǎn)角劃出尖銳聲響,我才看清擔架上人怎樣將鐵鏈與繃帶揉搓成一團——他的頜骨裂開半道,碎骨片刺進左耳根,卻仍緊咬著牙關(guān)不肯打麻醉劑。
"再過五分鐘就錯過最佳復位期。"主刀醫(yī)生攥著夾鉗的手微顫,"這傷勢要么截肢要么——"
"讓她來。"忽然有人扯開紗布粗暴截斷輸液管,消毒水四濺。我看見霍世安漠然抬起那只血淋淋的手,指節(jié)在白大褂袖口間探出時像刀刃切開空氣,"你說的第四個實習生,今年醫(yī)科院全A的林若?"
**
一、十字路口的初遇手術(shù)室的時鐘跳過三十二分三十三秒,剛好超過黃金救治期。但當那條斷掌重新貼合骨縫時,X光片顯示出毫米級的嚴絲合縫。我不敢抬頭看手術(shù)臺上的傷者——消毒水里熏得人眼淚汪汪,卻仍聽見他呼氣時鼻腔掠過的冷風。
"你的指節(jié)骨最近又長了半毫米。"他說這話時正被人縫合肱二頭肌腱,卻仍扯開創(chuàng)口邊緣的針腳。我握著持針器的手定在半空,直到白大褂領(lǐng)口滲進他身下浸濕的碘伏味。
"上個月看完的日劇。"他說著睜開眼,血珠順著睫毛垂落,"第三集主角就是靠這處掌骨斷口鑒定身份——"
"霍世安!"值班護士搶過止血鉗時連針管都摔在地上。
**
二、午夜鋼琴課三天后我在湖畔琴房撞見他。長椅推到墻角,樂譜被碾成紙團滾進排水口。當他弓著背扒在鋼琴鍵上時,指節(jié)骨硌出巴洛克時期的顫抖音。
"貝多芬?"我手撐著窗臺,望見月光穿過他的肩胛骨在琴鍵投下斷痕,"月光第三樂章改用布魯斯滑音?"
他的脊椎突然挺直。我這才看清那人右手食指貼著透明創(chuàng)可貼——正是三天前被我拗斷的骨膜的傷口。
"霍家的規(guī)矩是傷疤比琴鍵更需要撫摸。"他忽然轉(zhuǎn)身,羊絨大衣里的領(lǐng)口剛好露出左胸口那道縱貫整片胸肌的疤痕,"不然你覺得你救的是人?"
**
三、鏡中人相遇那天我們在三聯(lián)書店又撞衫了。他站在芥子園畫譜書架前的側(cè)影與鏡中重疊,直到川端康成的詩集跌進衣袖。
"無意識則不美。"我彎腰拾書時聽見他的腳步在玻璃鏡面前后徘徊,最終停在我后頸的領(lǐng)口,"連醫(yī)生標配白大褂都穿得這么松,難道不知道——"
"霍先生?"女店員捧著燙金藏書票走來時,才發(fā)現(xiàn)他已將書脊上嵌著的燙金字母轉(zhuǎn)成反向摩爾斯密碼,暗刻著那處疤的經(jīng)緯度。
當我們在咖啡廳重新相遇時,湖面倒映出雙份卡布奇諾上的漩渦。他用勺子攪動奶泡時指節(jié)劃出半圈弧線——恰如三天前手術(shù)室里創(chuàng)可貼撕開的角度。
**
窗外梧桐墜著整片新綠,空調(diào)外機轟鳴間我聞到碘伏里滲進的雪茄味。這是霍世安在科室第三次強行加床,卻從不讓人靠近半米之內(nèi)。直到那日他忽然摘下所有防護裝備——才發(fā)現(xiàn)胸前紋身并非刀疤,而是紫藤攀在鈦合金植入骨上的形態(tài)。
"七年前我這樣摸你的掌心時,你在手術(shù)室門口扒著門框比現(xiàn)在還要倔強。"他說著摩挲我第五掌骨,那里有個被消毒水洗淡的繭子,"這可是個……危險職業(yè)。"